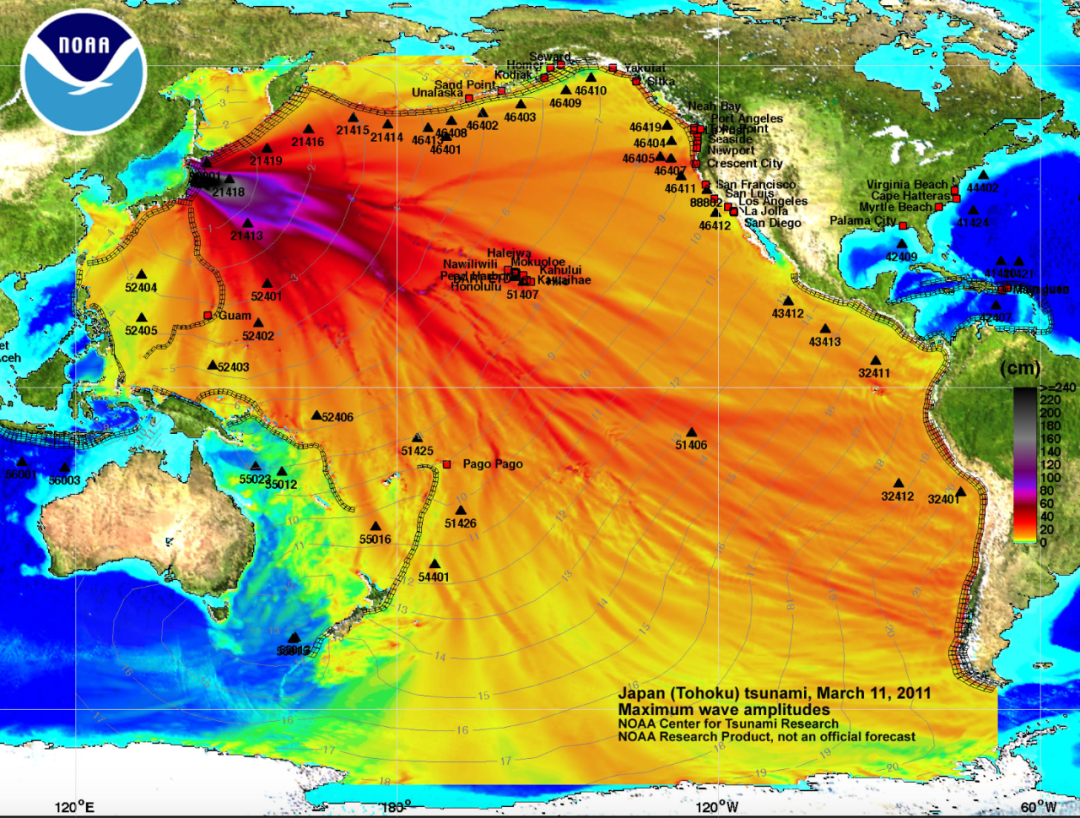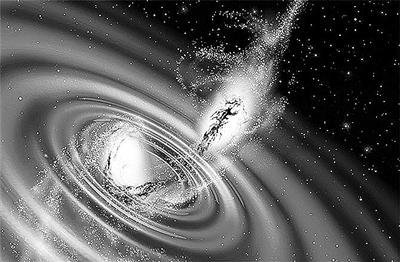怀念上世纪70年代的人和事
田兰桥
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一直到退休,我几乎在力学所工作了一辈子,回想刚来所时的人和事,仍倍感亲切和有趣,随手记之,以示怀念。
一、爆炸洞建设中的逸闻趣事
70年代初,我调到力学所并分配在爆炸力学研究室,刚到所工作不久即参加爆炸洞的建设。大家都知道,爆炸洞紧靠着北四环,占地3000多平米,东西长约100米,南北长约30米。内部以爆炸洞为中心,周围建有电测、激光、高速摄影等实验室。现在看来在这里建个爆炸洞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,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这同样也不是容易的事,但为了爆炸力学的发展,经过层层审批终得以批准。
爆炸洞的建设从设计到施工完全是我所的科技人员自力更生完成的,即自行设计、自行施工。我到力学所时,爆炸洞的建设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。爆炸力学研究室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建洞工作。除了我们外,大约还有一些工人 师傅和一个连队的解放军战士参加了建设。
研究室的所有同志每天到建设工地上班,包括钱寿易先生、郑哲敏先生也时时到工地来。从运送钢筋、水泥、沙子、砖头、木材等等建筑材料,到绑钢筋、和水泥、搭脚手架、砌砖等等建筑工人的活计,我们研究室的同志都能干。这其中不乏有许多逸闻趣事。
将和好的水泥运送并倒入料口,几乎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工作。这说起来容易,干起来可没那么容易。运送水泥的小推车是独轮的,掌握平衡十分重要。我看着那些男同志,或高大魁梧,或瘦小精干,平时走路四平八稳,书卷气四溢。但推起小车,个个是曲腿哈腰、摇摇晃晃,加之工地路面坑洼,经常会看到还没到料口,小车突然一歪,一车水泥倾车而出,在大家的笑声中,不少人提着铁锹赶去抢救。
爆炸洞整体由水泥现浇筑而成,中间有多层钢筋加固,所以绑钢筋十分重要。这些平时拿惯笔杆子的手,要改拿1尺多长,2、3厘米粗细的锥形钢钎,并快速地把几根不同粗细的钢筋牢牢地绑在一起,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记得好像选出了几个人去学习,由师傅专门教授这个技术活。刚开始上岗的头两天,他们神情紧张、小心翼翼、一言不发,即便如此,还常有不合格的,大家自觉返工。几天后,绑得熟练了,于是速度也快了起来,且边绑边调侃、聊天。然而危险也潜伏于不经意之间。一天,不知何故,在上面绑钢筋的一位仁兄不小心钢钎脱手,一斤多重的钢钎快速地直直落下,正好落在下面一位工人师傅的头上,万幸的是这位师傅戴着安全帽,只是肩部受点皮肉之伤。于是全体人员加强安全意识,工作期间不许闲聊。此事之后,工地落寂了一段时日,不久,又恢复了热烈、热闹的景象。
随着墙体的增高,脚手架要不时地搭搭、拆拆。在上个世纪,没有现在这种组合式铁制脚手架,都是用衫木现搭起来的。搭脚手架的杉篙很长,需两个人动作协调,同时抬起,一同放下。有意思的是,如此简单的事情,这些学富五车的“老九”[注]也能干出花样来。有的同志人在干活,脑子在思考问题。于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:一个人已经抬起一头,另一人站着发呆,或本应在喊“一、二、三,放”后一起将杉篙扔下,却常常刚喊到“二”时一方已经扔下,结果不是砸着自己或对方的脚,就是把对方拉个趔趄。因我年纪最小,老同志时时提醒我和别人抬杉篙时要小心,但我还是多次被砸,所幸并无大碍,却收获了多个“对不起”。
后来,领导让我跟着陆岳屏一起,负责爆炸洞顶部圆球浇注的木模工作。设计和计算,对于这些同志不是问题,但安装可就不是仅仅动动脑、动动嘴就可完成的了。木模要一圈一圈地围成圆形,和绑好的钢筋保持严格的距离,外圈再用特殊的钢带固定,之后开始浇筑水泥、再振捣,一层一层,直到顶部。记得大约浇注到三分之二时,再要向上安装木模了,一块模板怎么也找不到了。这时,有的说“不信找不到”,坚持满工地找;有的说再让工厂加工一块…… 七嘴八舌,吵吵了半天,问题没解决,但浇筑又不能停。这时上来一位师傅,拿着锯,胳膊下夹着几块板,一句话没说,量了量丢失模板的空档,噌噌噌几下就把板子锯好、安好了。这时一个声音传出“这不就行了嘛,白吵吵半天”,众人愣了一下,随即众笑,皆大欢喜。
爆炸洞的建立,为爆炸力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基地,为爆炸力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,也使初来力学所的我受到了一次锻炼。这是我在爆炸力学室的一段往事。
二、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当文化大革命渐渐进入尾声时,科研工作也逐步正常开展起来。我参加了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研究组的工作,段祝平是我的课题组长。在最初和他工作期间,我很不适应他的工作方法,主要问题是他的“善变”。
记得那时所里刚开始开展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研究工作,我们必须从建设备开始。我负责根据大家讨论的方案,并参考国外的资料,设计并绘制出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图纸,再交由工厂加工。然而这段时间让我颇感头疼的是,往往图纸刚完成,即将送往工厂加工时,段祝平又提出更改意见。如果是个别更改,倒也没大问题,改就是了。而有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,即一处尺寸改动随之几乎一套图纸的尺寸都要改变。
让我记忆尤深的是一套试件架和试件尺寸的设计和更改过程。在出图之前,全组进行了讨论,然后我来出图,一天下班前我完成了全部图纸,交给段祝平看后,他同意第二天送到工厂去加工。第二天刚上班,我正准备把图纸送往工厂,老段却叫住我说,昨晚他想了想,试件的尺寸还是如何如何更好些。由于那时我对材料动态力学性能的力学知识很少,于是就按老段的建议对图纸进行了更改。图纸完成后,在一天下班前将图纸送到工厂。本以为这项工作告一段落,谁知第二天一早,老段却让我将图纸取回来,他说:经过反复考虑,他认为还是应再改动一下。是学工出身,工程上讲究方案一旦定下来不能随意改变。特别是出了图纸若要改变那是要十分慎重的。对此我很是不满和苦恼。
那时我和白以龙都住在城里,白以龙住三里河,我住西单。我们常常一同骑车回家,在路上经常交流工作情况,白以龙也经常给我讲一些力学知识。在那次来回更改图纸之后,我抱怨老段的思维变化太快。白以龙听我讲了过程后告诉我:老段的改变是从如何得到更好的实验结果考虑的。这正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,科学研究不是一成不变的,变的过程就是接近事物本质的过程。
白以龙的这段话使我感到科学研究和实施工程是有区别的。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逐渐适应了老段的“变”,而且认识并体会到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地创新,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就是要勇于创新,不断创新。这是我在材料力学性能研究室的一段往事。
三、郑先生教给我他在干校学到的方法
郑哲敏先生为人随和,但治学严谨,对研究人员,特别对是有点资历的“老”同志要求十分严厉。那时听老同志讲,有些老助研在做学术报告时经常被“挂黑板”,即回答不上大家提出的问题,尴尬地站在讲台上。这被大伙儿戏称为“挂黑板”。所以大家在做报告前都很认真准备,若郑先生在座就更加倍认真。
在一次郑先生参加的学术报告会上,我介绍了几种聚合物在不同的冲击速度下的变形及力学性能的变化。因为其中有些材料要用于复合装甲中,因此人们对其在承受高速冲击下的性能变化十分重视。我介绍了试件在不同的冲击速度下的应力、应变传感器测到的波形变化情况,以及试件变形情况,还有我们的实验结论。郑先生仔细地询问了实验过程,并让我将波形相关部分扩展开来,结合结论进行讲解。整个汇报过程还基本顺利,忽然郑先生问:试件受冲击后的温度是多少?由于我认为试件变形后的温度对性能变化影响不大,加之测温传感器在试件上不好安放,所以没有测过温度。现在听郑先生问起来,心中十分紧张,但还是以实相告:没有测。随后郑先生又问:试件受冲击后烫手不烫手?我介绍了几种材料受冲击后手感觉到的情况,有的稍稍有点烫,有的较温和,但不知它们确切的温度。
这时,郑先生并没有批评我,而是说起他在干校劳动的情况,特别提到:我在干校时杀猪褪毛,水的温度要在60度以上。没有温度计,别人告诉我一个办法,用手试试,手能放进去温度就低于60度,放不进去、烫手,那温度就在60度以上了。进而,郑先生讲解了温度效应对聚合物性能的影响,以及对其分子结构也会产生影响等问题。
会后一些老同志说,这是你作报告,要是你们组长做,那就得吃批评了。是的,在以后的接触中,我更深深地感到郑先生对年轻同志既有严格的要求,更多的是指导和教诲。我想,这里蕴含着老一辈力学家对后辈力学人的期望。
[注]:“老九”是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蔑称
关于作者——田兰桥

简介: 田兰桥,高级工程师。1946年12月出生。1970年7月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并留校任教。1973年11月调入力学所,先后在二室、十六室、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从事力学实验等研究工作。2003年退休,现任中国科学院老科协力学所分会理事。